副标题: ——在湖南晃县的日子里
编者按
翁淑馨同志是贺龙元帅的堂嫂,曾著有《我与贺龙》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,但该书只写到她1931年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现在她口述的《度尽劫波》一文恰好与该书衔接,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。此文首次发表,以飨读者。
度尽劫波
——在湖南晃县的日子里
(翁淑馨口述)
一、祸从天降
1931年初,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夏曦“左倾”路线的恶劣影响,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我与蹇先任(贺龙夫人)在鹤峰官地坪,已感到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,红军家属躲的躲,逃的逃。4月的一天,蹇先任的马兵(警卫员)叛变,企图出卖蹇先任,于是开枪打死马兵,惊动了敌人。瞬息之间,险象丛生。蹇先任交给我10块光洋,并断然说到:“事不宜迟,赶快逃命去吧!”
“逃命?要是逃不了命,我们今生今世也就从此永别了!”
“嫂子,快别这么讲,我的心都快碎了!快跑,快逃!再耽搁就来不及了!”
我就这样在慌忙之中与她匆匆惜别。没想到我与她都大难不死,34年后的1965年竟又在北京重逢。
当时,我孤身一人从官地坪向东跑,先到人潮溪,再向南到江垭,准备沿灃水到灃州去洪湖找周逸群他们。不料石门保安旅的罗效之封锁了通道,对红军和红军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。我只好改道南行,白天躲躲藏藏,夜间匆匆赶路,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故乡铜仁,见到了孤寡一人的老母。
回到铜仁之后,听不到革命歌声,看不到战火烽烟,感受不到紧急的军情,眼前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。我惊奇地发现我好像是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从1924年到1931年八年时光,所见所闻,所思所愿,使我这个八年前的闺阁女子思想开化了,行为勇敢了。就在1931年底,我选择了再婚。不再像母亲那样,我三岁时父亲去世,她受封建礼教的束缚,竟终生没有再嫁。
我的丈夫吴松培,在中南门开布店,商号吴茂记。他少年时随其父母从江西南昌丰城县来到铜仁,他有两个弟弟,都已成家立业。松培的亡妻留下一女,名叫吴柳枝,已是十八岁的少女。
1932年10月31日我生一子,取名如南,白白胖胖十分可人。为了照顾如南,特聘了一位奶妈,人称舒嫂,忠厚朴实。因为生意好,还请了一位管账的师傅。自我结婚一年多来,生意兴隆,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和谐欢乐的气氛之中。
但是,在我心中总有一种隐忧,担心我与贺龙、与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被人揭发,遭人暗算。因为自1924年我与贺敦武在铜仁结婚,然后随贺龙第一次北伐;1926年又从铜仁随贺龙第二次北伐,几乎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有人若要“点水”(揭发检举)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可是,我又想,吴松培是生意人,外来户,为人老实忠厚,不会与人结怨。我呢,虽是本地人,但我一个年青女子更不会与人结怨,母亲寡居,靠几亩薄田维生,一心念佛,慈善为本,似乎我的担心又是多余的。1933年初,军阀车鸣异突然驻军铜仁,旅部设在今铜仁中学位置。8月16日清晨6点,祸从天降!车鸣异的匪兵突然将我家团团围住,声称捉拿“共匪”、“异党”。
也是天大的幸运,我到母亲老家打葛冲去了;松培又去了他父亲家。于是匪兵一边吊打舒嫂,一边疯狂抢掠我的家产。不到三个小时,我的家被匪兵抢劫一空。我的儿子如南,幸得邻里提醒柳枝:“快抱走你弟弟!”柳枝才趁乱将如南抱走,而她因受此惊吓,得了一种怪病,无药可治,不久就去世了。
但是车鸣异非要抓到我这个“共匪”不可,竟从我们一个亲戚口中查获松培藏匿的地点,绳捆索绑押到旅部严刑拷打,上了踩杠,压折了双腿。半年之后,车鸣异撤出铜仁,松培被放了出来,也算是捡了一条命。
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告密的人竟是吴门至亲!人心难测,出卖亲友,他就不怕报应吗?
二、运交华盖
1934年初,松培伤疾初癒,我们一家三口便含悲忍泪地离开了铜仁这个是非之地,伤心之地,开始了数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。先是去镇赶(今湖南凤凰)给人打工,干了几年,稍有积蓄。但长期打工,终非长远之计,松培决心重整门户,我很是支持。当时,听说晃县龙溪口商贾云集,好做生意,便于1938年初来到龙溪口。龙溪口有龙溪水源出贵州万山,下入㵲水。紧靠河岸建有一大片房屋,我们便租得一间。龙溪口有江西会馆,老表甚多,松培便去找了会馆会长。会长对我们的遭遇十分同情,立即指定一个商号赊货,卖后结账。松培在街上摆了一个纸摊,卖些笔墨纸张,又因他毛笔行书还可以,每逢年节,主要是赶集时,便为人书写对联,代写书信,生意也还顺手。可以将就维持三个人的生活。
转眼端午节到了,有钱人家包粽子,杀鸭子,全家老小吃喝玩乐好不热闹。可是我们囊中羞涩,两手空空,唯恐刺伤南儿幼小的心灵,便去河边玩水捉鱼,转移孩子的视线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我们才从河边返回。我特意盛了一碗水,对松培说:“时节莫拿空过去,盛碗凉水下菖蒲,也算是过了节吧!”松培说好,也是图个吉利。我俯身问南儿:“今天你过端午节了吗?”他仰着头,高兴地说:“过节了!”听到他那稚嫩的声音,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,泪流满面。
俗话说,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一天上午,上节街突然失火,火大风急,火势十分凶猛,由于整条街全是木房,几个钟头便烧成一片瓦砾。我家仅抢救出一些日常用品,堆放在河岸上。
不料下午四点钟左右,忽听有人大呼:“洪水来了,洪水来了!”转眼之间,洪水把堆放的那些衣物冲得一干二净。
眼看一无所有,我断然对松培说:“你赶快回铜仁借贷救急,龙溪口待不住了,我们去老晃城,你回来后在车站附近找我。”于是,松培慌忙返回铜仁。老晃城并不大,但却是交通孔道。它西通贵州,西北通四川,西南通广西,商人、军人、难民经常往来,商机甚好。它虽叫“城”,其实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,老晃城距龙溪口大约五六里路,当天因无钱住店,经好心人指点,城东老营盘有一座破败的小庙,可以棲身。这座破庙蛛网密布、杂草丛生,污秽不堪。我找了一块木板,简单清扫了一下,铺上一些稻草,搂着南儿和衣而卧。
我哪里睡得着,看着熟睡的孩子,心里默默地唸到:“孩子,爹妈对不起你,小小的年纪就让你跟着我们受苦受难。”看到眼前的惨状,彻夜难眠,多少往事都一起涌上心头。
1924年,十八岁的我与贺龙的堂兄贺敦武结婚,经过两次北伐战争,1926年贺敦武升任旅长在湖北攻打吴佩孚时阵亡。1928年贺龙、周逸群在湖南洪家关起义,建立红色政权,我追随红军在湘鄂西进行游击战争,经历过枪林弹雨、血雨腥风,艰苦备尝,从未感到过孤独和无助。万万没有料到,落到今天的地步。抚今思昔,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三、不速之客
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!那天身无分文,眼看就要饿饭,这时,我带着南儿走出破庙,竟然在路边捡到一张十元钞票。我用它买了些鸡蛋、糯米、炉灶、碗筷在客车站旁卖起了甜酒汤圆、甜酒鸡蛋。当天一大卡车士兵,他们跳下汽车把我卖的食品全都买完。
次日,松培从铜仁赶回,也得到一笔友人资助。于是便在车站对面租下彭家未竣工的木房,稍事装修之后便开设了旅店。松培去买来几尺白布,写上“南昌旅社”四个大字挂了出去,就算是正式开业了。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,“南昌旅社”也初具规模,虽然与同一条街上的“西南旅社”、“太平洋旅社”、“大同旅社”相比差得很远,但总算有了一个立足之地,“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”。
有一天,来了一位远房的亲戚,她叫翁老梅,按照辈分我应称她姑妈。此人奸猾成性,尽做些贩卖鸦片,买卖丫头,包打官司之类为非作歹,伤天害理之事。那天,她拿了一些鸦片烟土来住店,为了逃避警宪每晚的检查,她要将烟土藏在我的内室,我高低不同意,双方争吵起来,松培见状,便很不客气地对她说:“这些年我们多灾多难,现在稍稍安顿下来,只能吃‘补药’,吃不得‘泻药’。你老人家做这些违法的生意莫来我家,不仅今天莫来,今后也莫来!”翁老梅“哼”了一声,气冲冲地拿起行李走了。
1938年夏天,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,自称是未婚夫妻。男的叫徐天爵,女的叫汪凤梅,要求住店。我们这个小旅店只有十几个房间,条件简陋。对此,徐汪二人并不嫌弃,提出要住离我们内室较近的二楼房间,并且这一住竟住了近半年之久。
住久了,人熟了,松培待他俩如同亲人一样,过年过节请他俩吃饭,有事也同他商量。我则经常去他房间打开水,擦桌椅,整理内务。期间,他二人在西南旅社举行婚礼,还特地要如南为新娘牵披纱合影。
徐天爵其人谈古论今,学问渊博。他对书法很有造诣,字写得好,还善于口书(用嘴咬着毛笔书写),为人十分儒雅。但是,我对徐天爵其人始终保持着警惕,不该问的不问,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看的不看。因此,我与他夫妇相处融洽,一团和气。
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,秦光远夫妇带着孩子来到南昌旅社。徐天爵与秦光远彼此是认识的,多年不见,免不了寒暄一番。
秦光远这个人很不平常,不仅与我是同乡,他原是贺敦武手下的团长,而且是拜把兄弟。敦武北伐阵亡后,秦光远接任旅长,后又参加南昌起义,是贺龙的亲密战友,得力战将。他与夫人此次前来,有些蹊跷。他原先只有三个男孩大雅、大雕、大双,这次多了一个,而且年龄也不符。我便拉着秦夫人到后面房间询问情况。
原来,秦光远竟是从延安来,受贺龙委托,把大女儿贺捷生带回后方抚养,因为秦光远没有女儿,便将贺捷生剃去头发,扮成男孩。我知道情况后,大为惊恐,先是立即派人把捷生送到龙溪口刘见清家。刘见清是一年前如南认的干爹,比较可靠。
我又让松培去买了一瓶茅台酒,以为秦光远接风洗尘为名,邀徐天爵陪客,徐十分高兴,喝得酩酊大醉,也不再对秦盘根问底了。事后秦光远伸出大拇指对我说:“大嫂,你真了不起!今天好险啊!”第二天一早,秦光远夫妇就去龙溪口接上捷生离开了晃县。
不久,徐天爵夫妇离开南昌旅社,临走前竟坦诚地告诉我:“我是XX局的科长,是来监视你的。你的姑母翁老梅告你通共,有重大嫌疑,上级派我来查访。我住这么久,你与大哥为人很好,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共产党活动,明天我要走了,向上面汇报,说你们是良民,你们要多加小心啊!”
是啊,“多加小心!”小心火,小心水,小心人,尤其是小人,哪怕他是远亲甚至近亲。就这样在那战火横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,我们苦苦挣扎,小心翼翼,艰难苦恨繁霜鬓,终于熬到了1948年,我们举家回到了离别十五年之久的故乡铜仁,见到了满头白发的母亲。回乡后的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了,一个崭新的世界给广大中国人民也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安详!过去那笼罩着的种种劫波终于渡到了尽头。
(吴如南、吴如嵩记录、回忆整理)
附1:
吴如嵩教授简介

吴如嵩教授,系翁淑馨老人次子,贵州省铜仁市人,1940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晃县老晃城,即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晃洲社区晃州路居民组。1962年7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,10月入伍海军。1963年从海军调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(今战略研究部)工作。1973年6月入党。历任研究员、室副主任、主任,系硕士、博士生导师,军队技术三级。他是中共十四大代表,全军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,“全军优秀科研工作者”。
吴如嵩教授在军事科研实践中,对以《孙子兵法》为重点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行深入挖掘研究,在古兵法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,在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,被业界誉为当今中国研究《孙子兵法》最权威的专家之一。曾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首席专家、高级顾问。他先后出版《孙子兵法浅说》、《孙子兵法新论》、《孙子兵法·孙膑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辞典》(主编)、《孙子校释》(主要作者)、《中国军事通史》(编委会第一常务副主任)等十余部专著。其中《孙子兵法浅说》出版后,重印20多次仍然供不应求;《孙子兵法·孙膑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与传统医学》两部著作先后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等4种文字,在海内外广泛发行。《中国军事通史》作为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,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。他曾发表百余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,应邀在日本、马来西亚进行《孙子兵法》学术交流。
附2:
《铜仁市志·人物·翁淑馨》影印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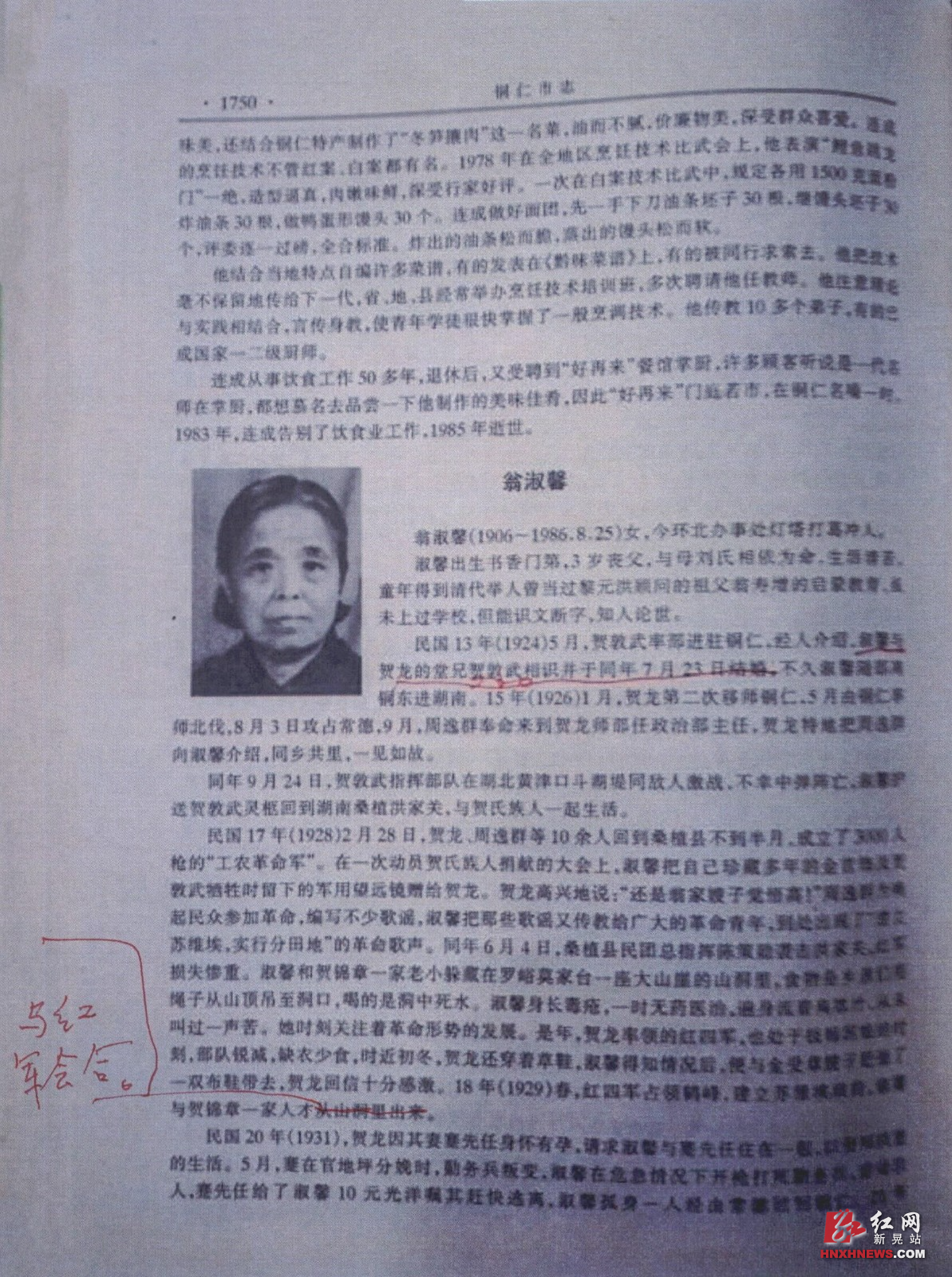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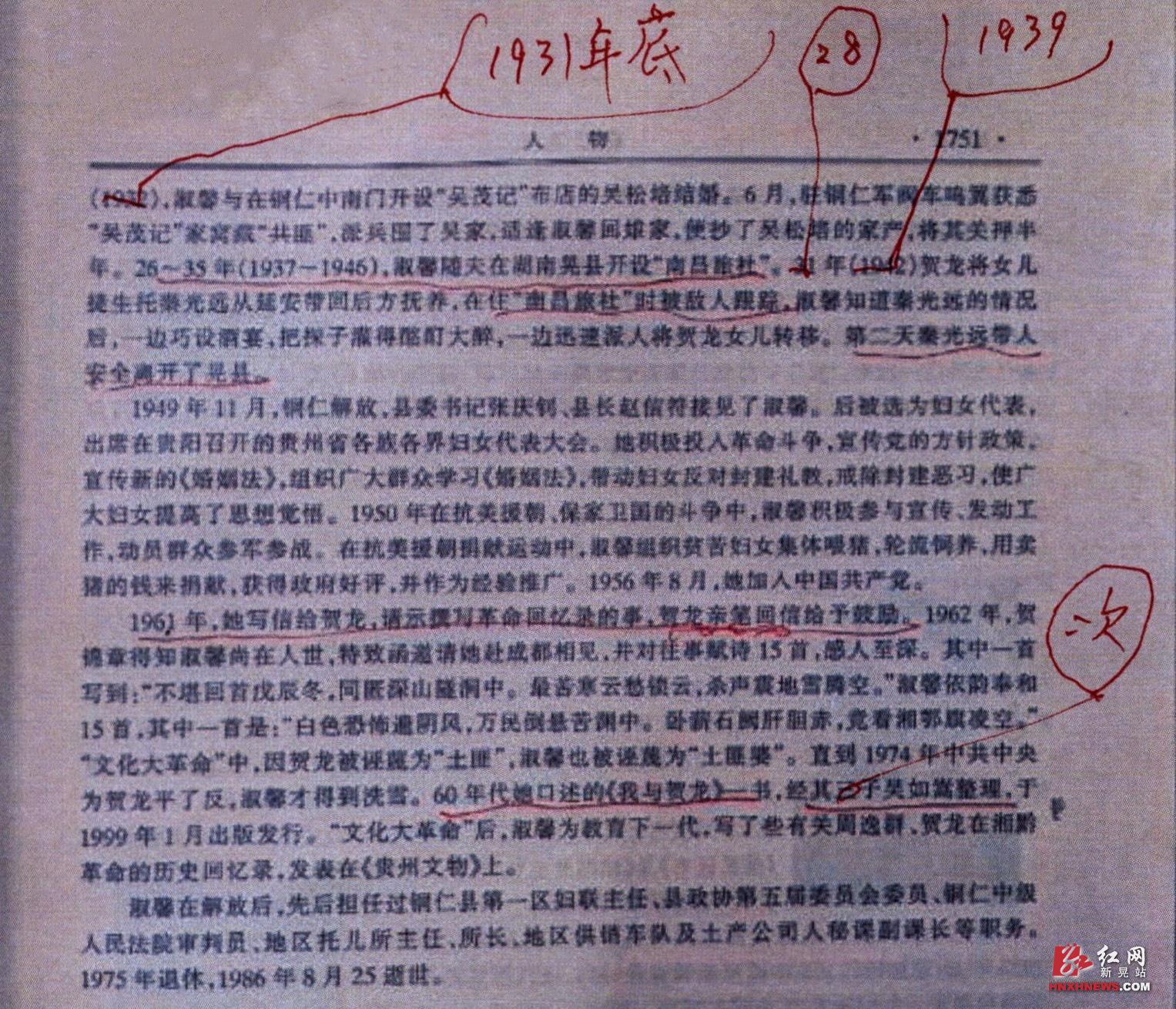
来源:《中共新晃史》编辑部
作者:胡爱国
编辑:张瑛
本文为新晃新闻网原创文章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。
本文链接:http://www.hnxhnews.com/content/2020/10/21/8534462.html